游戏论|《我的世界大电影》:毛茸茸的支配之球才不是方脑壳!
- 理财知识
- 2025-04-12 14:16:07
- 4

《我的世界大电影》剧照
2024年《我的世界》(Minecraft)游戏迈步进入第15周年,拿下2024金摇杆奖“爱不释手”奖(主机&PC端)。这款2009年5月由Mojang正式发布的游戏宣告正式迈入经典游戏的行列,时至今日依然还能源源不断吸引各年龄层的新玩家入坑“挖矿”。早在2019年《我的世界》就击败了同是方块像素美学的《俄罗斯方块》,以售出1.76亿份的数量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电子游戏。
2025年清明节期间,《我的世界大电影》(A Minecraft Movie)也带来了非常亮眼的票房成绩,在上映首周末就席卷1.57亿美元,成为电影史上最卖座的游戏改编电影,直接打破此前《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The Super Mario Bros. Movie)1.46亿美元的成绩。本片与同样是今年在中国上映的《刺猬索尼克3》(Sonic the Hedgehog 3)相比(截至清明节后全球总票房4.95亿美元),虽然都拿下了当周各国票房冠军,但这个成绩显然更加优秀。
影游场域作品再次证明了自己强大的传播张力,它们早已不是单纯进行故事改写(adaptation theory),而是通过“电影重复游戏画面塑造的名场面,并将其重新改写为银幕叙事的全新章节,在此过程中不断形成互文性相似却不同的多重文本”[1]的“三重再现”进行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
就如施畅所说,“改编的对象是故事,跨媒介叙事的对象是世界”。前者是在互文性中不断延续自己在人类记忆中的生命力,而后者是在“被叙事唤起之后,进行扩展性的幻象世界”,最后形成故事世界(storyworld),并且“不再注重考察版本演变,而是注重媒介融合”,忠于原著也不再被当作品质,叙事不同版本即便有出入,也会被认为是共存地图下的扩散美学(aesthetics of proliferation)[2]。于是跨媒介叙事成功在不同屏幕、不同体裁中自由流动,并且把近现实、远空间、云在线等各媒体融合编织到一起,营造出属于后电影(post-cinema)时代的电子在场感(electronic presence)[3]。
不过《我的世界大电影》具备的游戏性与其他游戏化电影(gamic cinema)相比还有更加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它的游戏《我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封闭文本,而是一个由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游戏。出品方Mojang虽然将游戏阐释为“一款摆放方块并不断冒险的游戏”,但实际上该游戏中的“冒险”已不再只限于“冒险模式”下的故事,在无限资源创造模式下对自己想象力和可能性的冒险才是最受欢迎的部分。尽管“由玩家而非开发者创造的游戏素材和资源早已成为电子游戏的一部分”[4],但《我的世界》就如其中文译名一般,整个游戏就是完全由我(玩家)在全是方块像素组成的游戏中玩(即生产游戏内容),搭建自己世界的过程。
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已经从游戏升格为平台,大量频道主通过展示自己在《我的世界》中各种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成果,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或搭建虚拟舞台。
《我的世界》对云玩家(spectator-players)来说简直就是最受欢迎的一集,游戏官方直接提供了旁观模式,玩家完全可以从建造者变成凝视者,这意味着在游戏中自主搭建的数字手工作品被转化为非资本性的数字藏品(non-fungible token)。“看=玩=产”这一逻辑完全贯穿于游戏,游玩化(Ludification)也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热爱这款游戏的人。在《我的世界大电影》最有代表性的彩蛋,就是村庄中踱步而过的那只“戴着皇冠的猪”(史蒂夫评价“他不是国王,是个传奇”)。它就是Minecraft最伟大的玩家之一、油管1000万订阅、起床战争/土豆战争/MC Ultimate/ 第九届MCC冠军,血神(Technoblade)的化身。
所以《我的世界大电影》并不是改编,而是扩展。它只是以非常明显的游戏化电影的方式,提供一种发生在《我的世界》里的可能性,甚至是最老套的可能性——就连电影内的角色高中极客少年亨利(Henry),和电影外媒体烂番茄(新鲜度只有48%)都吐槽“这样的冒险展开实在是太滥俗了”,但这又如何呢?因为它做到了既要球体流动、又要方块建造,还要毛茸茸视觉的分形模型。

《我的世界大电影》剧照来自A而不是the的命名
A的流动:当冠词性作品登上银幕
其实电影标题本身早已标记出,它并不代表深度注意力(Deep Attention)模式下的传统、中心化叙事,而是超级注意力(Hyper Attention)模式下的多任务、多界面、多信息流快速切换模式[5]。
如本文一开始所列举的三部电影,我们就能看出其作品定位的差别。《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The Super Mario Bros. Movie)和《刺猬索尼克3》(Sonic the Hedgehog 3)片名中都标记了定冠词the,《我的世界大电影》(A Minecraft Movie)则是不定冠词A,这种冠词性也在名词性/动词性游戏批评范式之外提供了另一种新角度。
罗伯特·罗素在《论指称》(On Denoting)摹状词(description)研究中认为the是唯一指称,斯特劳斯虽然在《论指称》(On referring)中扬弃了罗素的理论,认为the的本质是预设(presupposition)而非断言。但不管是哪种认定,都符合任天堂认为《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是马里奥IP的正统权威改编,也是对经典角色完全掌控的符号垄断权。尤其该标记还着重区分了与1993年真人版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Super Mario Bros.)的关系,标明了此片为唯一合法叙事版本。《刺猬索尼克3》则是另一种语言哲学表述,即专名语法。通过特定标记,让索尼克从物种刺猬(a hedgehog)升格为神话符号,不仅强化角色品牌专有性,同时也通过the的标识,形成与马里奥的竞争话语,这背后亦是世嘉与任天堂漫长的市场竞争。
但《我的世界大电影》的“A”直接表明本片其实只是无数叙事可能性中的一种,这正与游戏本身的开放沙盒属性呼应,各种服务器和模组(Mods)赋予《我的世界》更多交互选择。罗素认为A只需存在至少一个实例即可,片名亦保留其他版本的逻辑空间。A并不是意义闭合,而是创造性邀请的信号,告诉观众/玩家,大家都是游戏的共创者。
海德格尔在存在论视角下,亦将the与a整合为两种不同的状态,the属于“现成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角色、场景已被彻底主题化,观众只需消费既定符号;a则是“上手状态”(Zuhandenheit),指的是工具在使用过程中与使用者达到高度融合的状态,craft一词正是同时拥有名词性/动词性的手艺/制作的双重符号。而《我的世界》早在3月就推出了电影联动DLC,复刻了电影中有的鞘翅飞行、首夜生存、潜入林地府邸等诸多挑战。很多资深游戏玩家在观影后也准备着手在游戏中再现电影剧情,这都是游戏中的自由建造与游戏外的衍生网络,这些玩家/频道主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可消费的人物设定(consumable persona),成为了大写的微名人(A microcelebrity)[6]。
The与A的区别在电影彩蛋设置中出现了强烈的歧见。无论是马里奥还是索尼克,其密集的游戏元素考据都是作为内部文本的文化考古者出现,是服务于任天堂或世嘉系列的符号强化。但《我的世界大电影》除了尽可能复现各种游戏内的彩蛋,如超低概率刷新的粉红羊、热爱挖矿的初始人物Steve、会爆炸的Crepper、可以用元素组合敲击就生成的工作台、无意间前往现实世界的绿袍尊者、一拉开关就出现的熔岩烤鸡;以及各种衍生周边,迅捷之鞋(衍生游戏《地下城》法器装备)、恶魂热气球(衍生游戏《传奇》的概念艺术)、Mod模组(导演就说,小男主亨利及其土豆发射器就代表富有创意的模组创作者);此外电影的CGI光影与渲染观感相较于预告片再度提升,也是呼应不同版本持续进化的《我的世界》游戏。
当然还有贯穿整部电影的核心道具,组成地球传送门(Earth Portal)方块的蓝色立方体,支配之球(Orb of Dominance)。它是方形球,在外壳上的字符是标准银河字母,按逆时针螺旋状阅读出现的是六个单词:铁(iron)、金(gold)、石(stone)、门(gate)、头(head)、家(home),其形状各不相同,正好组成几个常见的俄罗斯方块模样。

《我的世界大电影》剧照三个不同世代的男主角
Mine与Craft:游戏文化的多个面向
与craft一样,mine在游戏中既指向金矿(名词维度)本身,又指向挖矿这个行动(动词维度),于是它既指向游戏中的符号系统,又指向游戏机制本身。如前文所说,在《我的世界》里,玩游戏、生产游戏与看游戏在像素方块的不断建设中实现了统一。
不过孙静认为,“无论是名词还是动词,都还停留在游戏现象本身”,她在这二者之外提出程序修辞(procedural rhetoric),指的是从游戏的“形式元素传达出的意识形态批判”[7],这些附着于游戏身上的特定文化价值观与批评范式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部分。
正如《我的世界》在兼顾了名词性/动词性之外,mine同时也是一个物主代词,它本身亦成为craft的程序修辞,让“矿井/挖矿”跳出二元结构,或者说从音译“麦块”作为世界的游戏要素,转向意译“我的”这一共创者主体召唤。
《我的世界大电影》视野当然不只是个人叙事,更是扩展到整个美国流行文化的某个发展界面。电影基本剧情亦致敬了好莱坞电影《魔戒》三部曲,从亨利拿到支配之球被同伴称为佛罗多(Frodo Baggins)到玛戈尔莎领导的僵尸猪灵(Zombified Piglin),再到钢铁傀儡与猪灵大军对战的画面,都与“指环王”IP中的诸多名场景颇具相似。
而三位男主史蒂夫、垃圾侠和亨利的先后加入,则代表三种不同历史时期的游戏与文化风格。
男主角史蒂夫由杰克·布莱克(Jack Black)扮演。他作为摇滚乐队Tenacious D的主创,其作品早已成为诸多文化产品的配乐插曲,例如《勇敢者游戏》(1995-2026、出演)《金刚》、(2005、出演)、《废柴联盟》(2009、参演)、《功夫熊猫1-4》(2008-2024、配音)、《无主之地》(2024、参演)。他在本片中亦为《我的世界大电影》加入大量摇滚音乐元素。他单人所在的剧情里,大部分实现的是《我的世界》中的创造模式,用无限资源搭建属于自己的风格建筑。
但首先,他心心念念想做一名矿工,在洞穴里挖矿(mine),这也是《我的世界》里创造模式下最初的职业。这是对美国19世纪50年代西进运动淘金热(Gold Rush)的价值复原(re-staure),是反思型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的一种具象化。
如博伊姆(Svellana Boym)所说:“人的创造性(elan vital)抵御机械式的重复和预言,而允许我们探索意识的虚拟现实……记忆是融合感受中一种无法预计的冒险,在这里,语汇和触觉感受是重叠的”[8]。史蒂夫从作为小男孩开始就一直向往着挖矿,这份向往本身就是对过往记忆的个人叙事再生。虽然他并不知道洞穴之下是什么,但直到成为枯燥的程序员打工人后,还是为矿洞赋予了怀旧的乌托邦寓意。
史蒂夫放弃了模拟触觉(键盘,Keyboard)而拥抱现实触觉(镐,Pickaxe)。但这份质感并不完全真实,一直守在矿洞门口的老矿工的面容从未衰老,这意味着史蒂夫心心念念想要进入的矿洞是混合了淘金热过往与游戏化处理当下的产物,这更像是放置游戏的另一面:点击增量游戏(incremental games)。
2013年作为现代挂机/点击风格集大成的游戏《无尽的饼干》(Cookie Clicker)应运而生,它既是养老放置游戏,又是点击爆肝游戏,足以让玩家沉迷在母性的乌托邦中:“游戏数值在不断增殖与肥大(hypertrophy),游戏的进程却更像预设的算法无性繁殖式的自我展演”[9]。毕竟即便取得成就的数值是虚假的,但获得激励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快乐。这个巨大饼干的变奏意象,在后续剧情里正是小镇里的土豆生产厂的巨型logo,正好被亨利制作的失去平衡的火箭给撞了下来。
最后,当史蒂夫在矿洞里找到那个代表“淘金成功”且打开“主世界”的宝藏,即支配之球(Orb of Dominance)后,“我的世界”像素方块世界才真正为他打开。于是他开启了在无限创造中建造从庇护所到各种房屋城堡的旅途。在这一过程中,史蒂夫与建筑物处于同一视线并面向镜头,更像是把在视窗外凝视的观众当作观看模式下的玩家,他的快乐也是将自己的建筑成果成功转化为移动虚拟凝视(mobilized virtual gaze)下的数据景观(data-scape)。
另一个男主盖瑞特·加里森(垃圾侠),他的粉红猛男色夹克与异形T恤致敬了美国涅槃乐队(Nirvana)主唱库特·柯本(Kurt Cobain)。他所擅长的正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已经相当流行的摇杆街机游戏(Arcade game),而且是格斗游戏(Fighting Game)。他想通过整体拍卖的方式,为自己的游戏厅购得一台复古雅达利(Atari)游戏机,却发现里面一无所有。或许是因为这台游戏机已经出现在《我的世界》模组“史蒂夫的节目单”里的“大电影游戏厅”中。
雅达利游戏机中的经典游戏也是各种方块,分别有乒乓(Pong)、打砖块(Breakout)、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s)、吃豆人(Pac-Man)等。而美国发生雅达利大崩溃的时代(Atari Shock,1983),因为游戏《ET外星人》的质量太糟,以及雅达利上充斥着各种同质化的换皮垃圾游戏,让雅达利乃至整个北美本地游戏行业在四年内几乎销声匿迹。
这也是垃圾侠名字的由来之一,同时他所进行的整体拍卖也寓意着,他想从来自“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垃圾镇”中重新翻出过往游戏行业的黄金时代。这种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在一次又一次重新打复古游戏的过程中得到体验,就是为了“重建失去的家园和弥补记忆中的空缺”。
电影里也再现了垃圾侠一直在游戏框面显示器前玩的对战游戏——美式摔跤(Wrestling),那是他与鸡骑士(Chicken Jockey)的擂台赛。谁承想FTG这种对战游戏彻底改变了街机游戏厅里射击游戏(Shooting Game)盛行的氛围,如今又要被建造游戏所取代。
少年男主亨利则是极客的代表,他的科技动手能力与《我的世界》游戏所需要的创造精神非常合辙。也是他带来了从现实世界的薯片,在工作台上做出了主世界完全不存在的武器“土豆发射器”,这就是代表《我的世界》的模组创造者们不断改造并扩展游戏世界观的过程。
而他自己,虽然上演的是内向科技宅转校高中生被孤立的故事,但整个叙事节奏却带着一股2022年前后在TikTok上流行的模式化“美式霸凌”味儿。两位霸凌者的角色,高度形似最开始流行“美式霸凌”梗创作者jackjos3ph视频里的人物。
也是在亨利加入主世界之后,整个《我的世界》才真正开启了生存模式与冒险模式篇章。观众也才真正接触到多样复杂的玩法——从夜晚僵尸到随机村庄,从鞘翅飞行到林地府邸,从红石矿石(Redstone ore)到滑翔机车,从躲避末影人(Enderman)到大战猪灵……整个游戏地图以不同版本为之打开。
史蒂夫(淘金世代)→垃圾侠(婴儿潮世代)→亨利(α世代),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差值正好在半个世纪前后。他们却能同处于《我的世界》游戏之中并肩作战,这正是虚拟视窗美学所突出的“时间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time)特征。


《我的世界大电影》剧照毛茸茸的方块生物们
Movie的质感:游牧的毛毡
如果说《我的世界大电影》还有什么是游戏中不具备的特质,那当然就是附着在这些生物身上让其显得更加毛茸茸的毛毡(feutre)感。
不过在此之前,毛毡下的方块才是组成这个世界的本体。
德勒兹的块茎(rhizome)概念可以被当作另一个概念化的方块,它们都共同反对传统(游戏叙事)的树状层级结构,而是强调无中心、多入口的网络化生成。这每个方块既是独立存在的,又在不同方块的排列组合中重塑地表。电影亦是如此,整部电影的剧情很简单,并没有传统电影的单线程情结块,而是“没有开始和终结,只有中间”的空间生产。
主世界、下界依然在那里,它们并不是因为电影主角团所有人(包括丹尼斯狼)的离开就关闭这个方块空间。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装配体(assemblage)理论下,异质元素之间应该是临时性联结,并且可以自运转。电影中的红石电路就是这样一个抽象机器,可以将各种矿物、机械、铁轨等都装配为自动化装置,运作也不依赖预设程序,而是在史蒂夫搭建的轨道上自然连结。
主世界和下界的存在,分别对应着创造与破坏,它们本身亦是这个世界本身更大的方块。一旦在主世界挖矿挖到更下层,下界也会随着出现,其相似关系一如现实世界与主世界之间的地理结构。这三者本身也是装配体,它们同时具备了固化边界的辖域化(没有支配之球就无法通达),也包括突破边界的解辖域化力量(可以通过方块创造出之前从未出现的建筑)。
整个方块像素所形成的拟像,正是在逼真与拟真之间选择了超真实(Hyperreal)像素化模拟。柏拉图主义认为拟像是赝品,方块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网格化摹仿。但颠倒柏拉图主义的德勒兹则认为,拟像才是差异化的创造性表达,它既重复算法规则,又产生不可预见的神奇景观:
“拟像远非是一种新的根据,它吞噬了任何根据,它保证了一种普遍的坍塌,不过它作为积极的和快乐的事件、作为脱根据化(effondrement):‘每个洞穴之后都有另一个更深的洞穴敞开着,每个地面之下都有一个更加宽阔、奇异、丰富的地下世界,而且在所有的基底下面,在所有的基础下面都存在一个更深的至深之处。’”[10]
而在超真实之表面,毛毡选择了重构装配体的回归。
电影里最值得夸赞的视觉效果,就是各种毛茸茸的方块,它们是各种生物才专属的特质,标记着生物与物品之间的不同,也是对这些游戏生物的人格化赋权:那些方块且浑身毛茸的大蜜蜂、狼狗(丹尼斯)、相亲相爱的熊猫、鸡骑士身上的小僵尸和鸡,甚至即将变成岩浆烤鸡之前的鸡也是充满着毛茸质感。
从像素到方块再到毛茸,其间毛毡发挥着重要的编织作用,它“作为一种反-织物,不包含线的分离,不包含交织,只有一种通过鞣制(foulage)而形成的纤维的纠缠……所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聚合体”[11]。毛毡的出现,亦展布着一种连续的视觉流变:游戏中的单一要素团块(block)在无限拼缝(patchwork)后形成各种建筑和生物,最终形成一个“由并置的碎片所构成的无定形的组合”。而毛毡戏拟着织物的构造(texture)将这些装配体变成了“你尚未成为之物”,而不是“成为你自己之物”。最后,在屏幕上弥合了游戏中像素方块在大银幕上可能出现的过于锐利的刺点(Punctum),在写实与像素化之间寻找着影游融合跨媒介的平衡。
这种联觉效果就如汤姆·冈宁所说,是“为眼睛实现了留声机为耳朵做的事”(Doing for the Eye What the Phonograph Does for the Ear),也为眼睛实现了按键为手指做的事:它将视觉与触觉并置,同时兼顾了触觉中的触碰(touch)与触摸(feel)的双重模除(modulo),前者是建造过程中对方块的操作,后者是观看过程中对毛茸的联觉;同时这也是玩家通过手柄操作游戏内角色触击(tap)屏幕空间的过程,大拇指接触到十字按键后,这个手指/数字(digital)接口才是真正连接不同世界的传送门。

《我的世界大电影》剧照游走的村民
余论:支配之球才不是方脑壳!
“A”的冠词性、“Minecraft”的游戏性、“Movie”的毛毡性,以一种巧妙非中心、非固化、非线性方式形成了这部隶属于整个《我的世界》游戏的非等级制网状拓扑,观众完全可以把该片当作是游戏服务器下的某个不确定模组。它的多变与解离装配出一种“既球形、又方块,同时还毛茸”的柔顺固体(solides souples)。
当有毛发质感的猪灵女王玛戈尔莎对着中年大叔人类史蒂夫说,你这个“方不隆咚”(这种叫法为“圆不隆咚”的戏仿)脑袋的时候,倒不如直接用一句四川方言说史蒂夫是一个“方脑壳”——这就像对着一个蓝色方块将其命名为“支配之球”一样充满着相当有趣的脱离正轨的逃逸线(ligne de fuite)视角。
其实《我的世界大电影》里真正的逃逸线角色,并不是从现实世界来到主世界的主角团众人,而是完全处于懵懂状态的真正的方脑壳傻子村民。作为傻子的他一直穿着绿色的衣服,没有职业,一直在溜达与睡觉之间交替,作息毫无规律且无法转职,所以被揶揄为“绿袍尊者”。虽然他看上去更像一个bug,但Mojang官方却将其确认为一种独属于《我的世界》世界观的特性。
绿袍尊者其实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漫游者(flâneur),他的随意行走本身就是对这个像素方块世界的诗性测绘,不受到作为NPC必须限制在村庄内的规则约束,所以也真正只有他,才能在无意中以一种解辖域化状态从主世界游牧到现实世界。
而在现实世界里,迎接他而来的是另外两条“未知的、未曾遇见的、没有预先存在的目的地”的逃逸线:一是现代小镇夜空下的车水马龙,然后突如其来的迎面撞车;二是在与副校长玛琳对视后,随之而来是一见钟情的爱情。
在玛琳与他的对视和交流中,尤其是一开始毫无意义的“哼哼”拟声词,到后来两人都学会了对方的语言。观众才发现,绿袍尊者的张望(flânerie)是一种反凝视,一种对高度阶层化与规训化的社会的剥离。
而这,才是《我的世界》这个用户生成内容游戏真切的现时性(Jetztzeit)体验。
注释:
[1] 但愿.游戏论 |《刺猬索尼克3》:在影游场域中跑酷的三条路径[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0634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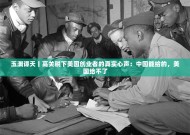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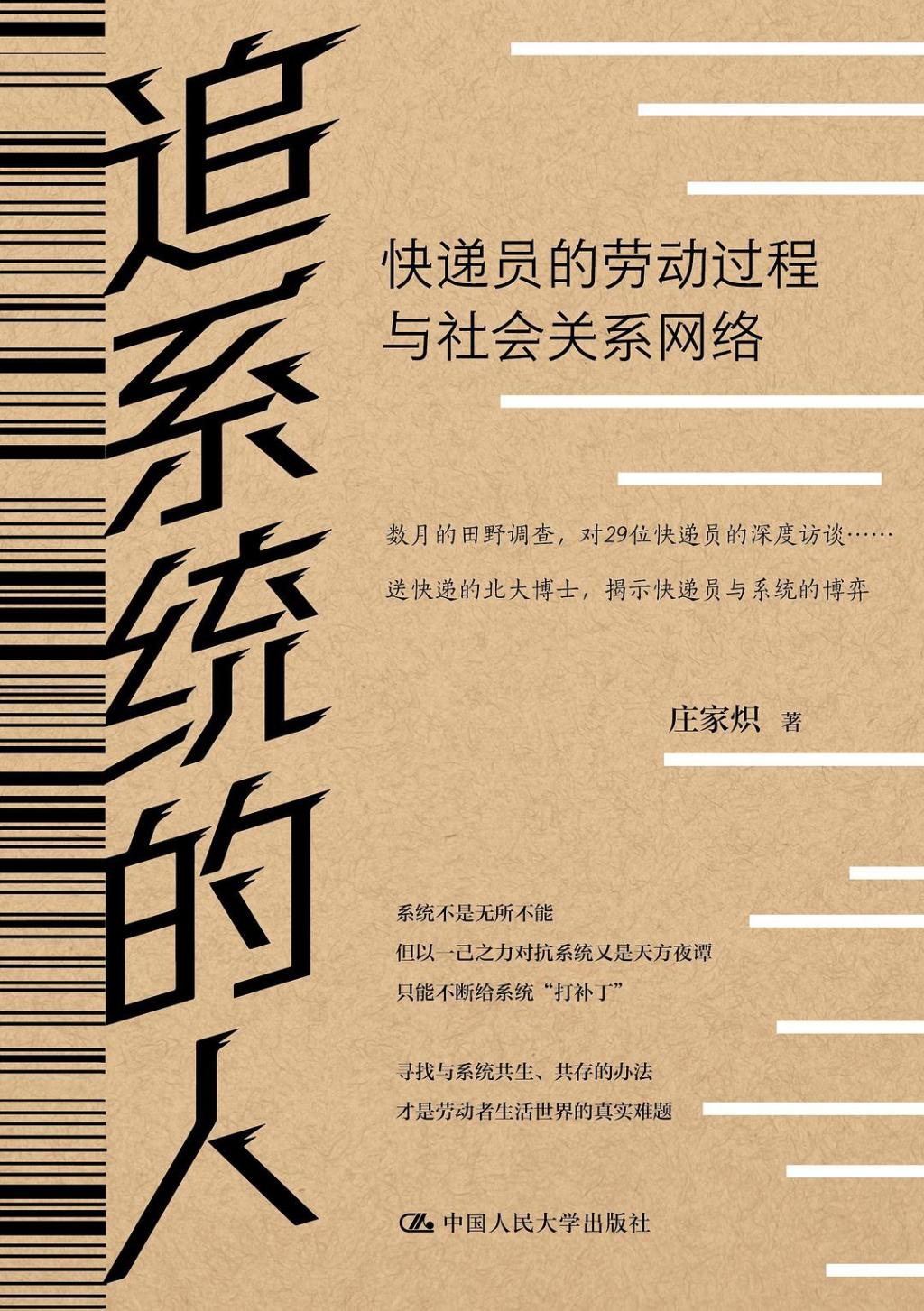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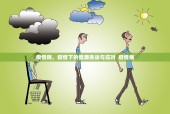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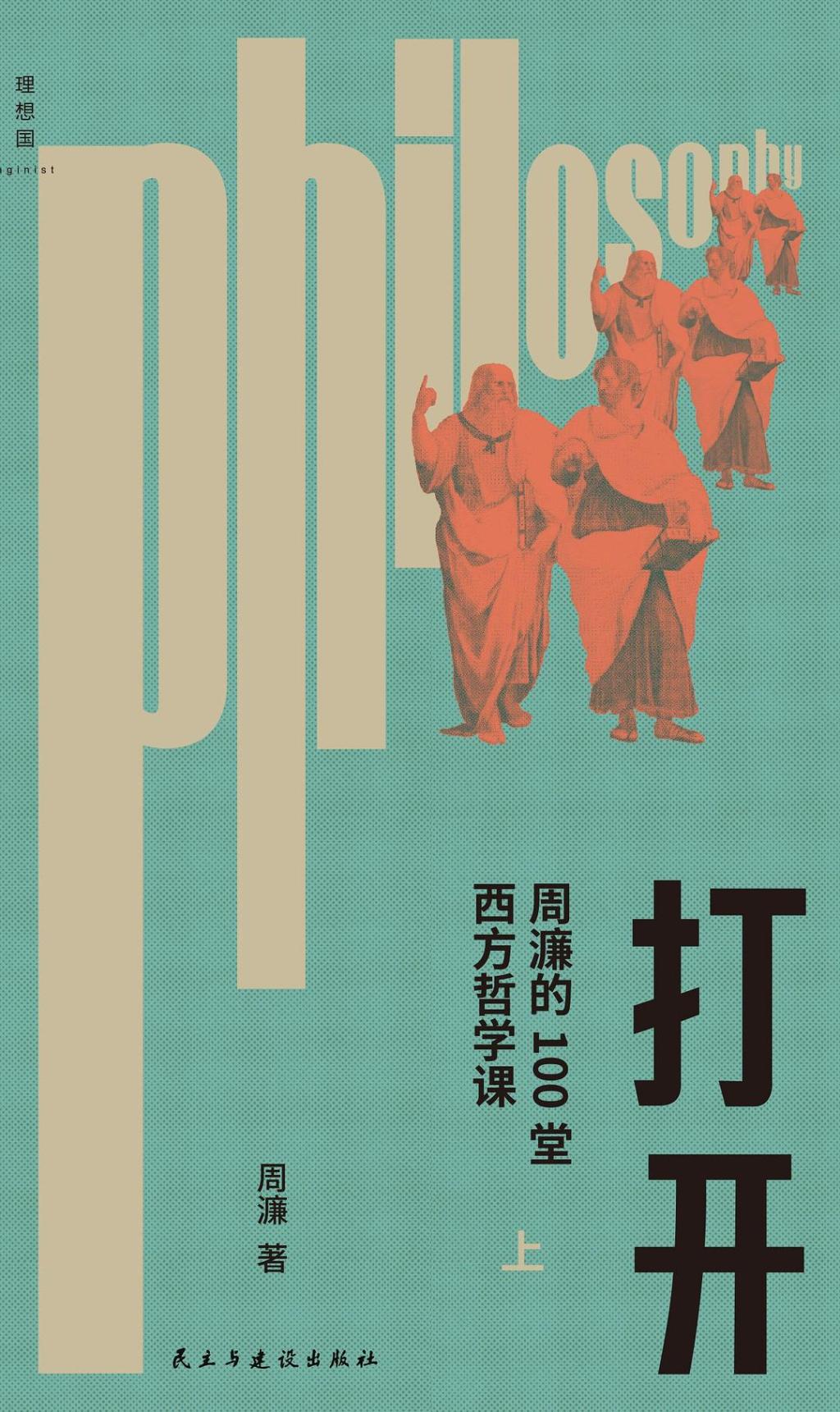

有话要说...